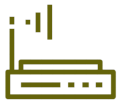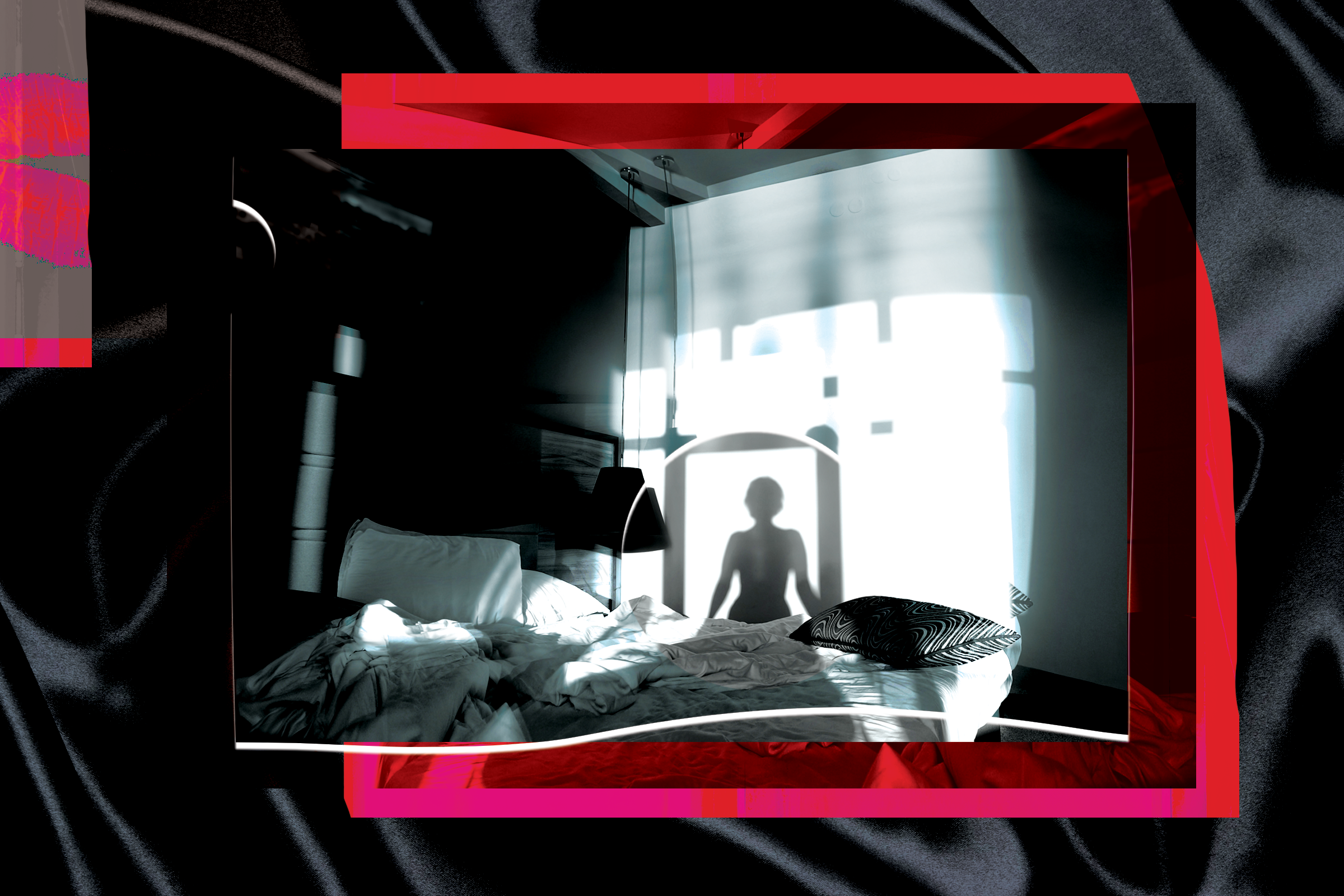
(SeaPRwire) – 過去十年裡,在我寫作一本小說的同時,我緊緊抓住了一個謊言。每天的大部分時間,我都會大聲地重複這個謊言,就像在祈禱一樣,希望可以減輕恐慌帶來的壓力,而這種壓力在那段時間裡主宰了我的大部分時間,至今仍未放手。這個謊言讓我能繼續寫作,雖然它很快就要破功了。我告訴自己,我絕不會讓任何人閱讀這本書。這就是我現在還在說的話。我只是在小說即將出版的幾天前寫下這些。我想到這一事實是不可避免的,恐慌又緊緊地抓住我。
我曾經私下和公開場合與朋友談論過這本小說引發的恐慌。如果被問到我擔心什麼,我提供過多種解釋,它們都屬實,但都不完整。首先,小說探討了多種慾望,包括肉體的渴望,其中大部分都帶有同性戀色彩;作為一個成長於韓國、天主教和福音派家庭的人,我很難擺脫自小就深深植根於我的三重性慾禁忌和罪惡感。我已經脫離宗教,但那些舊教條很難忘記。此外,小說中的人物大多是女性藝術家,她們都以高大的目標來激發自己的工作:我也是如此。這似乎意味著,只要透露這一點,我就會引來災難。(一位朋友曾說,「有抱負的女性」這個詞實際上是「不受歡迎的女性」的代碼;我問她是否連代碼都算。)此外,小說中的一位女性沒有忠於她深愛的丈夫;幾位藝術家也不願當家長。好像我列出了一份人們可能會認為女性不受歡迎,甚至會受到憎恨的理由清單,然後在寫這本小說時,一一實現了這些理由。
不過,我又在迴避,就像我一生中做過的那樣,對那個慾望,我在小說中最能描繪出來的慾望,我幾乎無法用言語表達。事實上,引起我最大恐慌的主要原因,能讓我陷入時長幾個小時的喘息、哭泣和錯覺自己快死了的假性但同樣強烈的信念,與一個我還沒有在這裡說出的詞有關:戀物。
這不是我第一次在寫作或談論戀物——2021年,我與Garth Greenwell共同編輯並出版了一本暢銷短篇小說合集,名為《戀物》。為支持這本書的出版,我也寫過文章,駁斥人們普遍存在且有害的關於戀物的信念,例如它是有害的、對女性不利的,需要治療的疾病等謬論。我在書面、音頻、網絡以及研討會和朗誦會上都談論過戀物。
但在那些言語洪流中,我從未洩露過自己的偏好。我用的語言保持一般性,通常用複數形式:我指的是《一些》人、《許多》人,以及群體、次文化和社區。如果覺得必須具體一點,我就暗示《某人》可能想要的東西。我熟練地以避免個人化的方式談論戀物;至少有幾位讀者抱怨,從他們看來,我似乎只是想出並共同編輯了一本關注戀物的短篇合集,但自己對它毫無興趣。我深信,這正是我需要做的:隱藏自己。或者說,出版這本書,但我自己仍掩藏在小說的不透明中,這種隱藏正是小說形式的重要組成部分。我依靠羅蘭·巴特的座右銘:larvatus prodeo,我以面具向前。
但現在,我寫了一整本小說,全都從一位同性戀韓裔美國女藝術家的視角講述,這位女性除了其他慾望外,也渴望探索戀物。我明白,人們很可能懷疑我——一位同性戀韓裔美國女藝術家——是否直接從自己的生活經歷中取材了小說中的所有事件。
儘管如此,我可能仍會繼續隱藏。畢竟,那仍是小說。而且,公開自己是同性戀已經足夠了,不是嗎?我很享受自己的同性戀身份;但對很多韓國裔人來說,同性戀仍被視為疾病。不久前——在韓國朝鮮王朝時期(1392年-1910年),法律規定如果一名韓國女性「過於」說話,就是可以成為離婚的理由。被驅逐後,一個女人如果無法自力更生,死亡就是她可能面臨的危險。也許我的身體已經不再記得這一點,但我現在卻在談論性和同性戀性。然而,這剛硬的面具和過去留下的規則,可能不如我想像中那樣有幫助,對我和寫作也沒有那麼大的幫助。
戀物是一個廣泛而不斷變化的詞彙,其定義取決於它不是什麼,而不是它是什麼。著名戀物作家兼播客Isadora Alman將戀物定義為任何性行為或實踐,只要稍微偏離你成長時被教導認為可以接受的範圍。因此,束縛、BDSM和戀物癖等都是戀物的例子,而且它們並不少見。根據某些數據,有;鑑於存在的污名化,這個數字可能偏低。
對我來說,戀物意味著玩弄控制。明確的權力動態;強烈的肉體感受,包括痛苦;規則——這些實踐對我體會性的理解來說是如此重要,沒有它們的話,慾望也會消失。它不是性行為的附加品。因此,沒有任何戀物元素的性,在任何個人重要的意義上,都不完全算是「性」。我可以追溯到記得渴望的時候,就知道這一點是真實的;同樣長的時間裡,我都認為應該保密,否則人們會認為我的渴望有問題。與朋友談論慾望時,我覺得他們說的話很奇怪。為了安全,我點頭附和。我假裝和他們一樣。第一個吻,最初的性活動:它們都不令人滿意,但我還是配合著。
直到我遇到將成為丈夫的人後,在約會幾個月後,我才開始勉強解釋。由於戀物對我來說和同性戀、女性、韓國人、人、生命一樣重要,我覺得應該給他機會逃跑。
有人可能會問,那又怎麼樣呢?戀物已經在公共場所顯眼地出現,甚至有一定程度的時尚色彩,這超出我成長時能想像的範圍。在大城市,不但網絡上,實體聚會場所也存在。只要有手機,任何人都不必再像我以前一樣擔心終生無法滿足戀物慾望。人們會在社交媒體個人資料和交友網站裡提到戀物。在我活動的文人、編輯和藝術家圈子裡,批評某人的戀物傾向已經不再時尚,反而可能被視為可笑。那麼,我在寫這篇文章時,手為什麼還在顫抖,好像我的手指正催促我停下來重新隱藏呢?
不久前,被吸引於戀物還被視為疾病。直到2013年,BDSM和戀物癖才從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(DSM)中移除,這本手冊對工作和撫養權具有法律影響。雖然戀物在流行文化中出現的頻率比以前高,但它往往與嚴重的心理傷害或邪惡掛鈎,這使我玩起一個無用的遊戲:如果一個電影或電視劇人物,比如一名連環殺手或駭人聽聞的壞人,我會追蹤需要多長時間才會出現與戀物有關的內容。通常五到十分鐘我就會證實自己的猜測。
所以,人們對戀物的謬誤也不足為奇。《戀物》出版的第一天,最憤慨的回應來自我從未見過的一些作家和編輯,他們堅稱戀物是有害和厭女的,是一種疾病。(簡單說明一下,對任何對此議題不熟悉的人:即使是最粗暴的戀物實踐,也與虐待有明顯區別——明確、詳細的同意,而不是一些人通過戀物獲得的治癒過程,也不代表它一定有特定的成因。)即使在我的更開放圈子裡,人們也常常質疑小說人物的戀物傾向是為了什麼,為何出現,好像它是可選的,而不是對我來說如此重要。
本文由第三方廠商內容提供者提供。SeaPRwire (https://www.seaprwire.com/)對此不作任何保證或陳述。
分類: 頭條新聞,日常新聞
SeaPRwire為公司和機構提供全球新聞稿發佈,覆蓋超過6,500個媒體庫、86,000名編輯和記者,以及350萬以上終端桌面和手機App。SeaPRwire支持英、日、德、韓、法、俄、印尼、馬來、越南、中文等多種語言新聞稿發佈。
如果成年人對戀物仍感到困惑,那對青少年來說就不足為奇了。